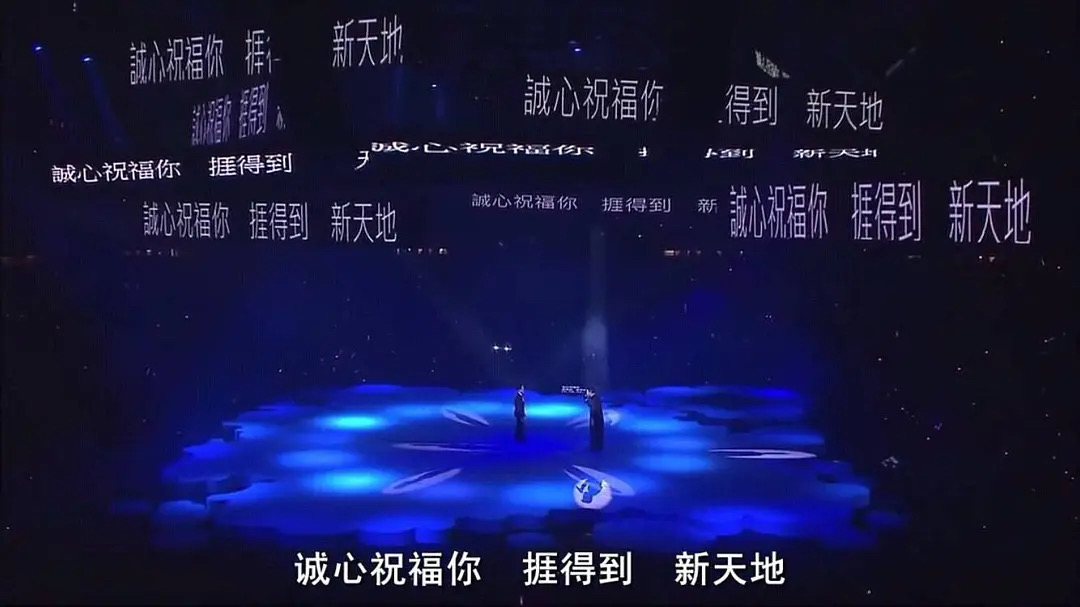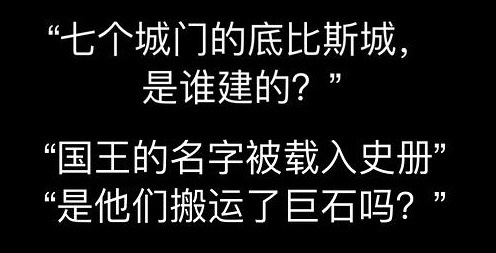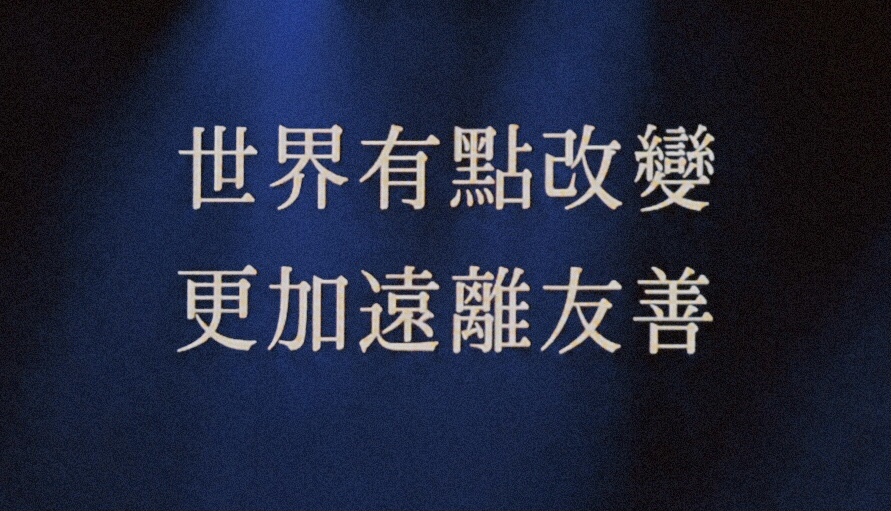伞遮不住雨,即使是
铁铸的
天样大的伞
周梦蝶
面对压抑与痛苦时,想要尽快摆脱它们是人之常情,从我们经常喊的“毁灭吧,赶紧的”中就可见一斑。在面对一个人们对民主自由求而不得的国家时,恨恨地希望它最好明天——不,最好是下一秒、立刻、马上大厦崩塌才好,实在是完完全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仅仅靠着这份恨意,恐怕很难实现这个目标。而面对模糊的前路,谁会不想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呢?
最近经历了一场争论,首先是一位群友说中国的一切都应该否定,中国人也不例外。接着就有人质问这位“你是不是‘支黑’?”然后也发言说你们这样的人太可怕了,这不就是想搞“献忠”吗?我话放在这里,如果现实中见到这样的人,我也会对等地见一个杀一个。
之后,被指为“支黑”的群友没有说话,但质问ta的人情绪激动了很久。不停表示这简直是类似纳粹、南京大屠杀的行径,自己绝对不能容忍。如果有人胆敢对自己的家人做出这样的伤害,那么自己绝对要对等报复。甚至说着说着,扬言要“清理”这样观点的人。
这时另一位群友安抚说:“你真的认为ta(被指为”支黑“的群友)会出门在街上乱砍吗?首先这个人可能并不是你所谓的‘支黑’,其次,那些认为‘中国人该死’的人有几个真的会实施这样的暴力行为呢?不要把自己吓坏了。”
当街砍人、无差别伤人都是令人恐惧的社会事件,最恐怖之处就在于它的发生可以说是无法预料的——其实无需对那位群友说“如果你对等报复,不就是变成了你最厌恶的那种人吗?”,因为ta所说的对“支黑”见一个杀一个也是很难实现的目标——正因为其无法预料、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由“个人”负责的事情。
这明明是一个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所应该负责的。
如果不假思索地想要凭借个人的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后果可能不仅仅是轻而易举地免除了政府本该承担的责任。例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个人或者小群体要如何永绝此类灾祸?可能需要借助网络科学手段,监控和分析居民的日常发言和一举一动,藉此发现隐藏的“杀人狂”;如果认为效率不高,可能还需要鼓励人们相互告发;如果发现了疑似“杀人狂”的人不止一个,那么为了安全考虑应当把他们全都控制起来;为了防止其中有人与他人有密谋,还需要控制他们的家人和社交圈子;如果最终无法确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坏人”,可能最终所有这些人都要为这份“安全”而做出牺牲。
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这个结果是“令人感到安全、安心”的。
又例如说想要全盘否定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其实这到底是个啥我还搞不太清楚,汉人的?中原的?儒家的?黄老的?中特的?)的人们,其内心想必也是愤懑乃至绝望的。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所有人的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更美好的向往——即使是说”我想要的只是毁灭“的人,如果在毁灭后依旧活了下来,难道不还是要面临着如何重建生活的问题吗?若是要重建生活,文化一定是无法摆脱的一环。其实在欧洲的历史里,“黑暗的中世纪”中天主教也成为了剥夺人的自由和人权的“工具”。然而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和斗争,宗教却能够成为捍卫民主、自由、尊严的“天赋人权”之出处。
我并非说我们只能固守“中国文化”,绝不能对所谓西方文明讲“拿来”。只是如果有人声称要弃绝、否定“仁义礼智信”,那么,这个人真的能够真诚地接受“自由、平等、民主、尊重、博爱”吗?普天之下其实无人不知自由之可贵,只是锁在手脚上的镣铐让我们无法立时得到它。如果因为人们被制度所约束而无法尽情追求更好的价值而认为他们生来就不配得到更好的,甚至认为他们只能世世代代被奴役或者只能等待毁灭,实在是太过不公平。
例如说元旦时,“我们视频”发出了一条探访疫情下的农村老人生活状况的视频。缺少药物的老人的药物来源只有儿女或者村中的卫生站,如果实在身体不适,儿女们也需要联系生产队前去探望老人的情况。当被问及基础病药物的钱从何而来时,老人们的回答都是乡村医疗补助。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居民保障支出只占总GDP的3.2%,着实少得可怜。但是对于老人和他们在外打工的儿女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保障。如果连这一点保障也失去,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真正的天塌下来。因此,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在“动态清零”期间吃了许多苦头的人依然会对“躺匪”恨之入骨。
然而这之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希望。在“封城”和放开后,全国诸多城市的居民互助活动其实比政府的服务无论在效率还是可靠性上都高出了许多,这无疑增加了居民们与社区等“官方机构”谈判时的底气——人们并非麻木不仁,只是没有选择。
我当然知道,中国并非是一个它所说的法治国家。但是,拿最近的“动态清零”的三年来说,并不是没有过因为人们在例如“国务院小程序”、“市长热线”等平台反映执法乱象而最终使事件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的行动,而且并非少数。再加上如今的抖音、微博平台发展壮大,设置了舆情管控措施的政府机关也不得不对其中响亮的声音作出回应。虽然我们心中都清楚,并非我们要求的每一件事都会得到回应,更遑论理想的结果,但这样一个(虽说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循)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黑箱”不正是说明了每个人的行动都有可能引发改变吗?行动永远都不会是无意义的。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是的。8964的枪响依然令人心碎,34年的光阴里,多少荒唐、多少牺牲。良心犯的名单越来越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有名字被记录上去。他们在站出来时,岂会没有想过“此后我将再也无法有自己的清净生活”?如果中共可以用“不能忘记先辈的鲜血”来为自己如今的统治提供合理性,那么为了不让勇敢的人们的努力白费,我们选择发出声音、努力行动难道不是更加合理吗?
历史中,野蛮战胜文明并非罕见,文明的成果也常常毁于一旦。但是,被毁灭的结果难道就可以证明这一价值是不值得追求的吗?若是总要确保自己能够在一场争斗中处于胜利者的地位,这不仅是人类无法做到的,同时也无疑是最懦弱犬儒的做法——它已然抛弃了自己的判断。要想永不失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结果出现时对自己拼命催眠。
可是这算什么正确的道路呢?
“的确,我们需要希望:没有希望地行动与生活,是超出我们力量之外的。然而我们并不贪婪,我们无需太多的赐予。我们不需要确定性。”
然而雨就是雨,即使千年万年,此地彼地。
伞遮不住雨。
Views: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