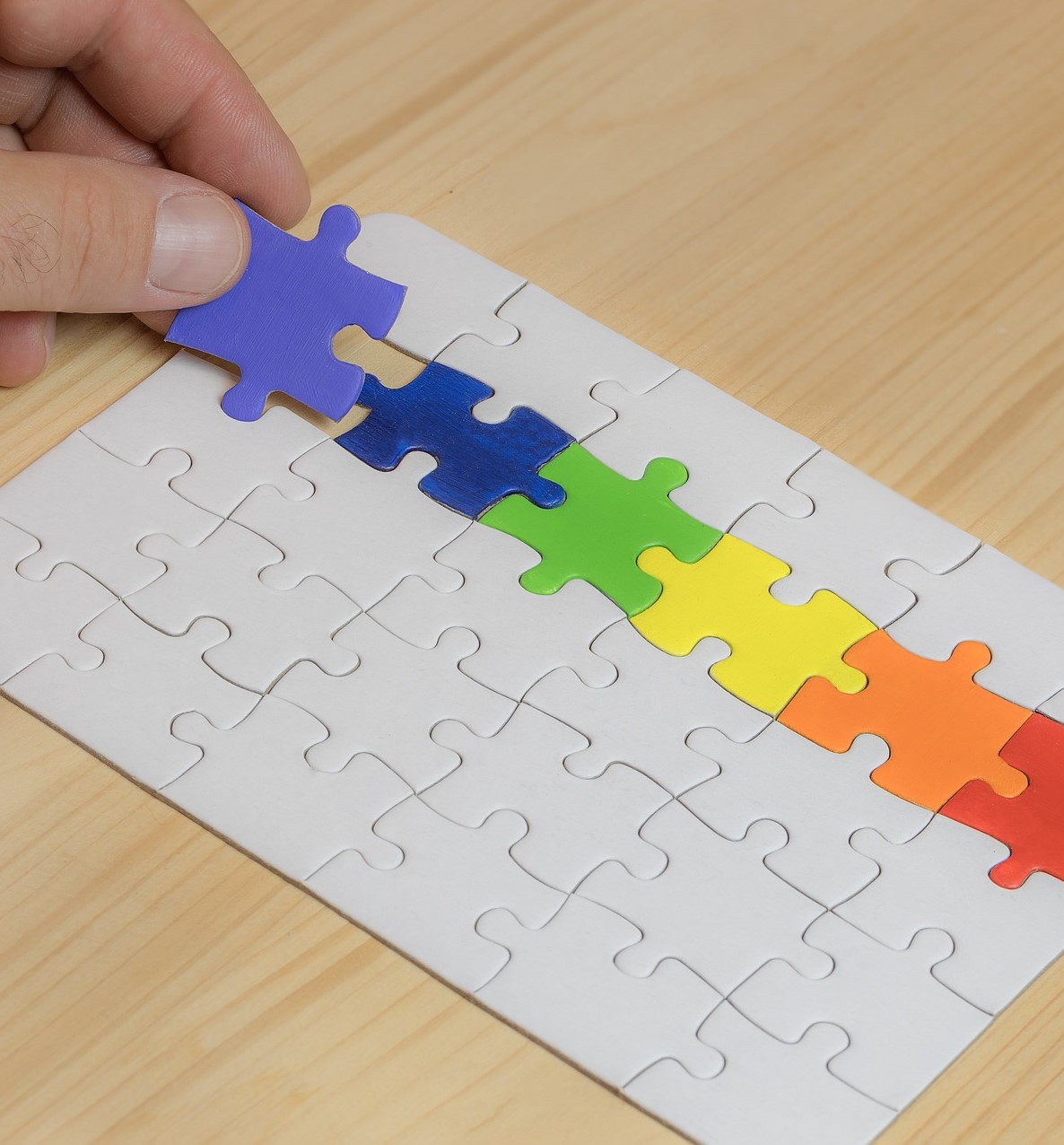前几天一个直人朋友问我:“你采访有没有涉及gay圈的艾滋病问题?这个比较敏感。”
我问她:“是不是说起同性恋,就会联想到艾滋病?”
她说因为看过艾滋病报告,里面大篇幅谈近几年艾滋病新增在男同性恋当中,而且青少年化非常严重。
这段时间,几乎每一个和我交流过的男同性恋,都会提到艾滋病。我在男同小组才潜了一个多月水,就见到一例新增。
我做同性恋亚文化研究,如果回避艾滋病,那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981年,美国洛杉矶三家不同的医院发现五例病患出现罕见的肺部感染1。
随后在纽约、旧金山都出现罕见的感染病例,所有的患者都是男同性恋2。
以前这类感染只出现在有免疫缺陷的患者中,从未发生在青壮年男性身上。
当时医学界将这类神秘的感染性疾病叫做“和男同性恋相关的免疫缺陷”Gay Related Immunodeficiency,(GRID),坊间称之为“男同性恋癌症”(Gay Cancer)。
1982年,美国疾控中心将此疾病命名为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根据英文缩写AIDS,中文将其音译为“艾滋病”。
1984年,科学家成功检测到致病病毒,将其命名为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今天众人周知的HIV3。
通过疾病的命名史就能看出,就像Covid-19不应该被称作Wuhan Virus一样,科学界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脱绑,希望少数人群不为疾病背负污名。
尽管如此,艾滋病一直和男同性恋的形象高度捆绑。
同性恋本是少数人群,携带HIV的同性恋边缘程度更深一层。
边缘人群的人数少,又常处于弱势群体,社会影响力低。
为什么他们值得社会学家投入大量精力关注?
除了社会运行需要人文关怀这类高大上的理由,还有一大原因: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直接折射出主流社会的运行方式。
今天和大家见面的张晨,叠加了同性恋、HIV携带者和心理病患多重身份于一身。
他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生活浓度远高于普通人。
张晨,25岁,本科,男同性恋,未婚,坐标珠三角
如果我回到年轻以后我会怎么做,我可能会好好读书,快快去赚钱,少约炮,多恋爱,多锻炼身体,对小时候的我好一些。
文:叶眉
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小时候父母经商,家里经济条件好,我们全家去泡温泉,我就隐隐有意识。
我有电脑,上网查相关的信息。那时候的网络氛围很好,我从爱白网获得了多数关于同性恋的科普。
爱白网的星星博士在网上做关于性少数人群的严肃科普,还主持问答专栏。
星星博士在我心里的地位比李银河还高。
基佬多少都有点女性气质。
我体型瘦小,从小学到初中一直被霸凌,过得解离又自闭,行尸走肉一样,看世界像隔了一层毛玻璃。
我初二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所以在学校小有名气。
校长怕我自杀自残,隔壁老师很关心我,女老师爱我心思细腻,我也更努力更好学。
我中学就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
有一次,初中老师以为我在补作业,当着全班的面看了我的日记。
他下课后来找我,只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当时的老师都知道我是同性恋,多数老师都对我挺好的。
除了一次,有个男老师让我为他口交,我告诉一位女老师,女老师还护着他。
很多同性恋一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性向会害怕、厌恶自己。
可能因为我通过很科学的渠道了解这些事情,在初中阶段,我很顺利地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完成作为同性恋的心理认同。
我一点都没怕过我自己,只害怕别人不接受我。
我第一次约炮是初三,那年我十五岁。
起初我并没想约。
我上同志论坛,加了本地QQ群,认识了一个男人。
他当时二十七八九岁,也知道我多大年纪。
我以为去见网友,可能会发展出一段浪漫爱情,能获得他的关爱。
那个年代我还没手机。我把他的电话记在小纸条上,坐车到他家附近,用小卖部的公用电话给他打电话,他来接我。
我这方面的运气也很好。
十五岁去见一个网上认识的陌生人,没被他拐卖或者五马分尸了。
但是我并没打算第一次见面就跟人上床,他诱导我。
他教我如何用套,如何保护自己,教我完整的流程,我至今都按这个流程走。
那时候我很迷恋他,我们相处了几个月。
他和我交往的时候,十分注意保护他的隐私。 我对这个人了解得非常少。
他比我大十几岁,会管教我。
他又不是我爸,没生我没养我,凭什么管我?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就分手了。
分手后,我就出柜了,问我爸妈能无条件地爱孩子吗?我妈反应不算激烈,我爸对我很不屑,厌恶,说同性恋都是变态,羞辱我。
我老师同学反而接受得很好。
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后来才意识到,那人是恋童癖。
但是我的第一次性经历不是跟他,而是和我表哥。
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我表哥大概十八岁。
他让我为他口,我就口了。
当时并没觉得这样做有问题,也从来没人告诉过我这有问题。
如果当年有大人引导教育,我可能会更好一些,不至于十五岁就独自去见网友。
我高三的时候在商场偶遇过那恋童癖,他跟在我屁股后面跟我聊天、“叙旧”。
我走在人多的地方,觉得特别惶恐恶心,全身发抖。
现在我身边有太多十几岁的小朋友就有活跃的性生活了。
我当年运气好没被拐卖。
不过建议小朋友无论约炮还是面基,都在人多的公共场合先见面,去哪里去做什么之前都要跟朋友通一下气,如果到时间没回家,请朋友打电话确认一下安全。
高中我住校,和爸妈分开了。
我爸妈生意出了问题,还经常上演家庭伦理大戏,自己的生活都忙不过来,没空管孩子。
我高中重新做人,过得很爽。
我加入了学校的杂志社,杂志社里三男三女。三个男的都是基佬,三个女的都是腐女。
我们想做一期LGBTQ的科普专题,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取向,性别气质等等这些。主编很支持。
我们把样刊都做出来了,结果校长那关通不过。
在杂志社玩得很开心,我对其中一个男生表白过。
他那时候还是深柜,没完成自我认同。
他表面上拒绝了我,背地里沉迷耽美小说,真是笑死人。
我和另一个男生变成了好姐妹。
基佬之间称“姐妹“类似闺蜜,是好朋友,不会上床。
很多人恐同,以为同性恋见到同性就想把TA扑倒。
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所有异性见到TA都会想把TA扑倒吗?为什么觉得同性恋就见一个扑一个?
我们高中是全封闭式学校。
十几岁的人,和父母分离,被逼着独立。
我看国产电视剧父母大战青春期的孩子觉得很可笑。
我们那时候连见父母的面都不容易,坐下来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很少,哪有机会跟父母吵架?
我和同学、朋友、舍友、老师相处,寻求同辈之间支持。
爸妈不接受我无所谓的。我就是要交男朋友,就是不结婚。
我高中三年,伴侣就没断过。
我回翻日记,有十八个记得名字的性伴侣。我和他们类似恋爱关系。
曾经有一个服装设计的大专生,正准备毕业,找工作,和我谈了一两个月,后来他要上班,就回老家了。他事业很成功,衣锦还乡。
有一个小区保安,人生经历很坎坷,辗转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他满足了我的制服幻想。
还有一任是拉丁舞老师,他在读舞蹈硕士。他很有女性气质,很温柔,浑身都透着艺术感,非常美。
他带我去看展览。我蛮享受和他的关系的。
还有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叔,成熟、成功、自信。
他虽然年纪比我大很多,但是不管我。我迷恋他活得自由自在,有困难困惑都找他。
我和他在一起时间很长。
曾经遇到一个十二三岁出柜被父母赶出家门的人。
他在酒吧陪酒,也曾被包养,好的坏的都试过,他对生活都不抱希望了。
我也遇过天赋不足但是技巧好的人,凭借后天努力赢得地位。
基佬最懂男人。
我们知道男人天生不会忠诚。
男人都爱找刺激,精虫上脑,什么都顾不上了。
男同在伦理上没那么多约束,从来没听说过“我初夜给了你,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你要为我负责”这类话。
那个年纪的男孩子精力无处发泄,不受管束,也不听教。直男打架,基佬约炮。
高考体检的时候,医生发现我的肺部有淋巴结,一开始还以为是其他问题,查下来,我确诊了艾滋病。
HIV攻击人体的免疫系统。
测量人体免疫力的指标叫CD4。
普通人的CD4在400-500左右,我确诊的时候才100多。
医生说,这个数字意味着我已经感染一段时间了。
我拿到确诊书,躺了两天。
我一直都用套,不知道怎么感染的。
也许是口交,也许有人中途摘套我没察觉,也许套破了,不知道。
我马上要高考,顾不得那么多,也没想追究是谁传染给我的。
我当时想的是千万别害了别人,于是挨个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去体检。
我把能联系的人都联系了一遍,尽到我的义务了。后来也没听说他们当中有感染的。
我本想瞒着父母,但是我妈在我的房间里翻我的病例,发现了确诊书,我爸自然就知道了。
我妈不说话,也不安慰。而我爸,又是一顿羞辱,说了很多恶毒的话。
我妈把我的个人用品都换了一遍。
我爸的意思是将来我就藏在家里算了,开个网店讨生活,别出去和人接触。
我不指望他们能理解我。
初中时期我了解同性恋知识的时候就了解过艾滋病,知道它现在已经不致命了。
确诊后我也疯狂查资料,下了专门的软件,加入艾滋病互助组织“红树林”,大家互助交友。
医生给我配了“替拉依”组合药物,每天晚上吃三粒。

中国艾滋病患者服用的药物都是美国十几年前的配方。
美国现在主流抗HIV药物一天只需要吃一粒,而且副作用小。
但是进口药在中国销售过程很复杂,全自费一个月要一千多,普通人吃不起,还不一定总能配到,一旦断药就很麻烦。
老配方医保报销。
老配方,有些人会过敏,或者有严重的副作用,有后遗症。
我比较幸运,第一个配方就很适合我,也没出现过敏之类的反应。
当时我只期望降低病毒载量,提高CD4。
大概确诊后半年,我才知道艾滋病治疗的最终目标是UU,Undetectable=Untransmitable,就是HIV载量低到检测不到,也不具有传染性。
我现在就是UU的状态。
知道它是一回事,需要亲身处理是另一回事。
我确诊的时候只有十八岁,人生才刚开始。
高中过得像青春偶像剧,确诊后就成了《孽子》,一点都不轻盈。
我开始思考生命、性、和健康的事情。
官方做防艾宣传都是宏大叙事,个人经验完全不一样。
抗艾公益人张锦雄说过:“携带HIV的同性恋需要出柜两次,第一次是性取向,第二次是携带HIV。”
我面临的头号问题是如何告诉舍友我携带HIV。
当时很害怕,怕别人对我开恶毒的笑话,或者别人有偏见,也怕谣言。
当时一栋宿舍楼住一千多人,我不知道谣言会传成什么样。
如果我不主动告知,被别人发现了,会不会来敲诈我?
我很注意,水杯这些专门分开避免和别人混用,药就放在桌子上。
我每天晚上吃药,舍友看见自然会上网搜。
我们没明着说过,大家心照不宣。他们没什么反应。
确诊后我没折磨自己,很快就接受了。
但是我需要考虑:要不要谈恋爱?要不要约炮?发生关系之前要不要提前说?
曾经有女性朋友说:“怕传染病,不做就好了啊。”
人有欲望,怎么可能不做爱?
我大一那年都没有插入式性爱。
大一下学期,我遇到了一个人,一见钟情。
我们是天雷勾动地火的双向吸引,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爱。
因为谈了一年我都不肯和他发生关系,他以为我是清纯男大生。
后来我跟他坦白了。我病毒载量低,带套,不会传染。但是他过不了这关。
他当时是深柜,没完成自我认同,时常批判我的穿着打扮,令我很不舒服;我也发展出双相障碍,时而狂躁,时而抑郁。
我们的关系慢慢变得有毒。年末,我痛定思痛,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门口跟他提分手。
那里人来人往的,一米八的男人,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痛哭。
有些携带者会在社交软件上注明 “+”,“UU”,或者对暗号 “吃糖”之类的。
我没这样标注过。曾经我约过一个老外,他就大大方方地写明“UU”,我还挺羡慕他能这么坦荡的。
他标明“UU”是为了保护别人,而整体国内的氛围,告知对方,是为了保护自己,类似免责声明。
如果一夜情的话,我就不告诉对方我UU,但是不插入;如果是长期关系,我都会提前告知,同时严格带套。
我也会告诉身边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为得知我是HIV携带者而改变对我的态度。
我在另一个城市实习的时候,约过一个博士。他专门做性别研究,我们之间有很多交流的话题。
我对他超级上头,告诉他我是HIV携带者,他一点都不介意。
他平常在服用PreP阻断药物,以前也有过携带者伴侣。
我和他体会到了性•灵合一。
从他之后,我的固炮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
有些人生病后会自我隔绝,但我觉得, 性是性,病是病。
不能被洗脑将疾病和性挂钩。
女人生孩子死了的也不少,怎么没说女生怀孕是罪?
关键还是性教育,不要把性妖魔化,也不要把病妖魔化。
我大学期间在防艾NGO组织做过四年志愿者,见过很多触目惊心的案例。
现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更是良莠不齐,年轻人都没有正经渠道获取科学的信息,把耽美文、小黄文、A片当性教育材料。
不了解传染病的基本知识,更不了解做爱本质是交流,要交流、沟通、有共识才能有好的体验。
平常不戴套,事后发现对方携带HIV,甚至还可能遇到恶意传播的人。
他们暴露之后吓得半死,来问我怎么办。
我让他们赶快去医院开阻断药,72小时内紧急阻断还来得及。
我做志愿者接待的求助者都是大学生。
我们的性教育做得太差了,学校不教,父母不教。
大环境都假装性是不存在的,一旦冒出苗头就把它妖魔化,恐吓青少年。
一味吓唬,结果呢?能吓退吗?
他们都不知道同性恋就算不需要避孕也要带套防病。
除了HIV还有其他性传播的疾病,也只能靠套预防。
更不知道现在有HIV阻断药物事后补救,还有事前PreP药物预防HIV传染。
我每次都戴套都还感染了,因为安全套不是100%有效。
当年如果有PreP药物,我一定会常规吃。双重保护利人利己。
Blued和翻咔应该组织线下的区域性的活动,也只有他们有资源有渠道来做这些事情。
Blued只做了一个HIV快速检测的通道,顺丰当日送达,这远远不够。
线下的聚会真人互动,可以交流很多事情,也可以让年轻人获得更好的性教育信息,给同性恋更多的支持。
我曾经一度没办法控制情绪,没法健康生活。
大学时期有心理课。
我刚进教室门,老师就看出我不对劲,让我赶快去看心理医生,上课都没有看病重要。
中国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更少。我去看心理医生,首先要出柜,再讲精神领域的东西。
有些医生无法接纳同性恋,我就立刻换人。
我找专业的心理医生都很困难。
确诊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的双相障碍已经发展了好多年了,而且程度很深,怎么才来就医?
作为HIV携带者,我CD4指标200多。我问医生这个指标怎么样?医生说:“死不了。”
毕竟无论考公、考事业编,还是做教师什么都要体检。
HIV携带者像二等公民一样,缺乏社会通行证。
如果工作体检查出来HIV,经常会用其他借口开除。
现在我每半年去验一次血,去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一张“爱心门诊卡”,拿着卡就能拿到药,一次可以拿三个月的药。
拿药的时候有个专门的窗口,护士会叫名字,让病人在一个大本子上签名,上面写着谁什么时候,拿了什么药。
我觉得很不安全。
那个本子记录最隐私的信息,就摊在那里随便让人看。
现在每次出门旅行前我都会反复检查行李,确认带够了药。
因为一旦断药,病毒载量就会上升,CD4会下降,就有可能感染并发症。
而且病毒会耐药,原来的配方就不能吃了,非常棘手。
我免疫力低,身体瘦弱。这瘦不是健康的瘦,看上去就不健康,怎么吃都长不胖。
同性恋是少数人,携带HIV也是少数人,残疾、贫困、都是少数人。
偏远地区、农村、县城的艾滋病患者还可能看不到医生吃不起药呢,他们怎么办?
现在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就期望他们不要祸害人,其余都不管。
这么多年了,性教育和传染病教育都没有新的东西,没进步,信息不公开也不透明。
我喜欢一个人,要看他是不是gay,喜不喜欢我,能不能接受我的病, 能不能接受我的精神病,能不能陪我走疗愈自己的这段路。
正常人谈恋爱已经很需要运气,到我这里是中彩票。我不敢奢望。
采访手记:
我开启约炮调研课题以来,张晨是起始年纪最小的受访者。
我们聊了几天,他给我整体印象非常乐观豁达。
他说起生活的关键节点,总把“我运气好”挂在嘴边。
他生活经历很坎坷,但是我们共享了很多笑声。
他看过第一稿后问我:“我发现你没有提到我作为小朋友开始约炮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为什么呢?我当时是运气好,所以没有被五马分尸。可是小朋友约炮的确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他再一次提到“运气好”,我才意识到,我误解了之前“运气好”的意思。
我和过去的受访者交流,都问过他们是否担心安全问题。
女性一开始多少都有安全顾虑,然后发展出一套方法来筛选对象,保护自己。
而男性都没怕过。
但是我没问他。
我为什么会忽略这点?
我根据其他人的经验,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作为男性, 没有安全顾虑。
后来我跟他细聊,才知道他第一次去见网友,并不是完全自愿发生关系的。
根据潘绥铭和黄盈盈在2010年的调查数据,14-18岁之间的少男中,有24.4%遭遇过强迫的性行为4。
估计这数字把很多人吓一跳:怎么可能?接近1/4?为什么我平常没察觉?
性是极私密的领域,一般人不会对外说自己的性经历。
如果不是遇到社调,也难有启齿的机会。
于此对比,40.7%的少女有过被强迫性行为5。
这个数据虽然令人震惊,可能很多人反而觉得合理,少女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性侵的概率更大。
但是!注意!敲黑板!社会调查获取被调查者自我陈述(self-reported data),调查结果呈现的不是社会客观事实,而是行为主体的建构。
什么叫行为主体建构?
举个🌰:对方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我问他:“你刚才是否经历了危险?”他肯定说没有。他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就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脱险的。
女性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被教育:你要小心坏人,坐公交车小心咸猪手,晚上不要出门,穿着不要暴露……避免成为犯罪目标。
所以女性对这类行为非常警觉,经历这类场景,能辨识出对方来意不善。
男性成长过程中低估危险,一个很显著的结果是男性的意外死亡率一直比女性高6。
男性在性领域经历的客观危险场景难测量,但是我推断一定比调查数据更高。
很少大人会教育男孩:“你要小心,要保护自己,要警惕陌生人,警惕大人不怀好意欺负小孩……”
张晨回想起和表哥之间的经历,没觉得不对,也没人告诉他不对。
谈起第一次的对象,他的口气透露过一丝怨恨,因为两个人年龄差很大,生活经验和权力地位都不对等。他随即又转轻松,聊起古早时期的小卖部公用电话。
我一开始没意识到此事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后来他问我为什么不详细写那一块,我才意识到背后的权力结构。
张晨经常遇到十几岁出来约的中学生,他会直接拒绝。因为他也曾是受害者。
他聊高中时期五光十色的生活,语气欢快愉悦;说到确诊,口气立刻黯淡下来。
他也是我这段时间采访的,第一个向父母出柜男同性恋。
以前采访别人,我极少有带入感。
但是和他聊的时候,我不停地带入父母的角色。
孩子从小学到中学遭了这么多罪,父母在做什么?
父母得知孩子是同性恋,愤怒、羞辱都正常,但是事后冷静下来,应该会上网去疯狂补课,试图了解孩子。
临近高考,孩子确诊艾滋病,父母第一反应恐艾也很正常,事后应该去补课了解医学进展,了解HIV携带者的生活有什么特殊需求。
但是他的父母都没有提供支持。
他说起父母,没有怨恨,也不亲近。
他说:“我运气真的很好,一路走来有太多人爱我,陪伴我,关心我,宽容我,保护我。我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还活着,怎么能计较那么多?”
达明一派有一首歌,《爱在瘟疫蔓延时》,是专为艾滋病创作的。
歌里唱道:“心即使浪漫似烟,风沙将万念也变灰。”
张晨第一次跟我连线的时候,语气轻松愉快。后来几天,我们越聊越深入,他说的内容也越来越沉重。
灰暗得我都不愿意触碰。他不怎么盼望感情生活了,希望能治愈心理疾病。
张晨说:“有时候睡前我会想,如果我回到年轻以后我会怎么做,我可能会好好读书,快快去赚钱,少约炮,多恋爱,多锻炼身体,对小时候的我好一些。”
参考文献:
1、CDC. MMWR Weekly: pneumocystis pneumonia—Los Angeles.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1981;30(21):1-3. Accessed May 30, 2022,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june_5.htm
2、CDC. MMWR Weekly:Kaposi’s Sarcoma and Pneumocystis Pneumonia Among Homosexual Men — New York City and California.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1981;30(25): 305-308. Accessed May 30, 2022, http://www.jstor.com/stable/23300179
3、Curran JW,Jaffe HW, MMWR Weekly:AIDS: the Early Years and CDC’s Response.Supplements. 2011;60(04):64-69.Accessed May 30, 2022,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su6004a11.htm
4、潘绥铭,黄盈盈,(2013)《性之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Accessed June 4,2022,https://read.douban.com/reader/ebook/4658189/
5、Ibid.
6、Zhu, J., Cui, L., Wang, K. et al. Mortality pattern trends and disparities among Chinese from 2004 to 2016. BMC Public Health 19, 780 (2019). Accessed June 4,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9-7163-9
Visits: 92